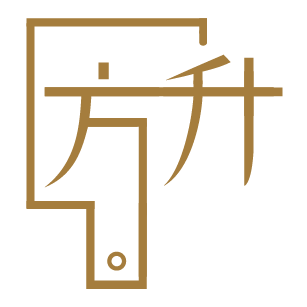税返闸门轰然落下,二三线城市招商引资注定再难翻身?
| 作者:七禾页 | 2025.08.28 10:50:39 | 阅读:43 | 报告下载 |
《公平竞争审查条例》一纸文件,把延续了二十多年的“税收优惠—财政返还—低价供地”连环招彻底锁死。最先感受到寒意的,并不是家底雄厚的一线城市,而是那些长期把“政策洼地”当招商引资“核心竞争力”的二三线城市。
过去的招商圣经一夜之间变成了负面清单。企业用脚投票的逻辑也随之改变:谁能给出更长的税收返还期、更高的返还比例,谁就能抢到项目——这样的故事已经落幕。如今,摆在二三线城市面前的问题,不再是“还能返多少”,而是“没了税返,我还能拿什么吸引企业?”更残酷的是,答案不像从前那样可以靠加码优惠来拖延,而是必须在产业逻辑、治理能力、资本市场乃至城市品牌上给出系统回应。

在税返盛行的年代,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地方需要GDP、就业和账面税收,企业需要低成本甚至负成本的经营环境。于是,“五免五减半”“地方留存全返”等条款被写进各式各样的投资协议。为了争夺一个上市公司总部注册地,部分城市甚至把返还比例抬到90%以上,财政倒贴也在所不惜。这种以未来税收作抵押的“杠杆招商”,一度让二三线城市在账面数据上实现了“弯道超车”。
然而,杠杆的另一端是不断累积的财政风险。审计署2023年通报,21个省份存在违规返还税收、低价供地等问题,涉及资金超过800亿元。当经济下行、土地财政吃紧,这笔钱成为随时可能爆炸的“或有负债”。更关键的是,税返扭曲了市场信号:企业选址不再遵循产业链、人才、市场的逻辑,而是沿着政策缝隙“游牧”。一旦优惠到期,便迁徙到下一座城市,留下一座座“注册经济”的空壳园区与空壳城市。
《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的核心正是堵住这条扭曲的赛道。条例明确,任何与税收、产值挂钩的奖补政策都必须接受公平竞争审查,“特定经营者”不得再享受差异化待遇。这意味着,过去那种“一对一”谈判、量身定制的返税协议失去了合法性,地方招商的“核武器”被拆除。
随之而来的,是各类项目流产,某中部省会城市2024年初与一家新能源龙头签订百亿级投资协议,核心条款是10年税收全返。该城市希望围绕这家新能源龙头企业带起一整条新能源产业链。但随着条例实施,协议被迫中止,企业也转而落在了长三角。对于这座城市而言,他失去的不只是一个项目,而是整个产业链的想象空间和金融资本的注意力。
这并非特例。随着相关条例的逐步实施,对于众多二三线城市来说,她们难以摆脱现有产业基础的束缚去进行有效招商,企业也不会仅凭空泛的故事就轻易投资。若缺乏税收优惠,又怎能吸引投资?当前,地方债务问题同样制约了产业投资的步伐,尤其是引进龙头企业,没有数十亿乃至上百亿的投资规模,对方根本不会考虑。然而随州200亿“假央企”事件仍历历在目,谁还敢轻易投入如此巨额的资金?
当然,在政绩高压之下,不专业的人往往会干预专业事务。为了追求短期成绩,仍有人会违规操作,只要能暂时掩盖问题,风险便留给后来者承担。这正是招商骗局屡次曝光却依然屡见不鲜的根源所在。
更难受的是,根据网络信息爆料,东莞本地调研情况显示,当地76%的企业在享受完政策红利后选择迁离,平均驻留周期仅2.7年。当税返不再续命,那些本就奔着补贴而来的企业开始集体“用脚投票”。一些城市一夜之间出现注册企业注销潮,税收缺口直接暴露在财政报表上。
当失去招商的源头活水,本地企业加速外流,二三线城市的招商引资翻不了身了吗?

税返的大门关闭,但产业竞争并没有停赛,只是换了赛道。企业依然要选址,地方政府依然要招商,双方都必须回到一个更古老的逻辑:城市和产业园区究竟能为企业创造什么样的真实价值?
如今的政策倒逼对于二三线城市的未来发展道路反而是一场意外收获,推动城市回到人、回到本土产业本身。当“返税”这张王牌被抽走,二三线城市反而卸下了“比拼优惠”的沉重枷锁,重新获得了因地制宜的从容。过去,为了和沿海强市“抢项目”,很多内地城市不得不把稀缺的财力砸向并不契合自身禀赋的产业,结果是“引进来”却“留不住”。
如今,条例像一把手术刀,割掉了畸形的政策肿瘤,也让地方主政者正视本土特色产业,这里的气候适合中药材生长,那就把中药材种植—初加工—提取—制剂的链条做厚;这里的稀土矿伴生金属丰富,那就围绕稀土永磁材料、电机、风电装备做垂直整合;这里的非遗手工技艺积淀深厚,那就把文化符号转化为IP,再把IP嵌入消费品供应链,变成可以规模化复制的“土特产2.0”。
没有了“返税”的幻觉,产业规划必须回到最朴素的逻辑:我有什么、我缺什么、我能补什么。贵州铜仁把“抹茶”做成世界单品冠军,靠的不是补贴,而是高海拔、多云雾、低纬度的独特小气候和20万亩标准化茶园;广西柳州螺蛳粉从街边小吃到百亿级产业,靠的是政府把酸笋、豆角、腐竹、米粉四条上游链条补齐,再引入电商仓配、金融结算、包装包材等生产性服务业。强链补链不再是口号,而是地方政府必须精算的“资产负债表”:缺一家包材厂就补一家,缺一条冷链就建一条,缺一级人才就联合职校定向培养。当链条完整到足以支撑一个产品在全国乃至全球市场的成本优势、速度优势和品质优势,企业自然用脚投票,而不再需要靠“税返”诱惑。
换句话说,《公平竞争审查条例》不仅是一纸禁令,更像一次产业体检:它让所有城市回到同一条起跑线,二三线城市相比一线城市虽然在产业发展领域存在一定差距,但也逼着二三线城市重新发现自身的不可替代性。当大家不再比谁“返得多”,而是比谁“链得深”“链得准”,那些真正理解本土资源禀赋、敢于深耕垂直赛道、愿意用时间换空间的城市,反而迎来了被税返时代掩盖的“逆袭窗口”。

1、产业链场景:对于二三线城市未来的产业发展必然是从“大而全”转向“小而美”,过去几乎所有城市都在追逐“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热门产业,结果是千园一面、互相内卷。如今对于二三线城市而言回到自身资源禀赋,深耕细分赛道反而更容易形成“产业锚点”,也更容易落实招商引资工作。
就像常熟用“羽绒服产业链”吸引了波司登、北面等龙头。前端有千亿级面辅料市场,后端有直播电商、跨境物流,企业不出30公里就能完成从设计到发货的全流程。宿迁把一瓶洋河大曲延伸到白酒小镇、包材供应链、电商直播基地。
当产业链足够厚,企业迁移的机会成本就会高到难以承受。
2、营商场景:营商环境是目前企业高度关注的“城市优惠”。在利润趋薄的存量竞争中,每缩短一天审批、每降低一次违约风险、每减少一次往返盖章,都直接转化为可量化的现金流与可折现的未来收益。营商环境因此成为地方政府唯一的持续输出型“政策红利”:它不靠财政输血,而以规则透明、服务高效、纠纷低成本来降低全生命周期交易费用。当补贴归零,资本与项目将自发流向制度成本最低的城市,营商环境的差异便直接决定招商引资的胜负。
长沙把“一件事一次办”写进地方性法规,企业开办时间从3天压缩到4小时;苏州工业园区推出“免审即享”政策,惠企资金直达企业账户,无需申报。这一系列看似不起眼的政策微创新,在税返时代被“大招”掩盖,如今却成为企业决策的关键变量。
3、资本场景:北京、上海、合肥等地正用千亿级产业基金取代税返。政府不再直接返钱,而是以LP身份入股子基金,撬动社会资本共同投资落地项目。资本招商的精髓在于“以投带引”:企业缺的不是几百万补贴,而是几亿甚至几十亿的股权融资,谁能提供资本通道,谁就拥有招商话语权。
对于二三线城市来说,与其复制北京、上海的“巨无霸”,不如做“小而准”的穿透式基金。把财政杠杆用在产业链最卡脖子的环节,二三线城市同样可以用“小基金”撬动“大项目”,把股权通道变成招商引资的话语权。

税返时代,招商像一场百米冲刺,二三线城市凭借“政策兴奋剂”拥有追击的能力,却往往在产业马拉松中后劲不足。条例的实施,把所有人拉回到同一起跑线:不再有“政策捷径”,只有“产业长跑”。
对于习惯了“立竿见影”的地方政府而言,阵痛不可避免:财政数据可能下滑,招商人员需要转型,甚至要接受一段时间内“项目荒”的煎熬。但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政策出清,都会带来一次城市格局的重新洗牌。那些愿意慢下来,深耕产业链、嫁接资本、优化治理的城市,终将在下一程竞争中脱颖而出。
毕竟,真正的好企业,从来不是冲着补贴来的,而是冲着“在这里能成事”来的。当二三线城市想明白了这一点,就会发现:税返的黄昏,恰恰是产业黎明的开始。